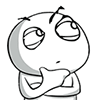图书介绍
- 作者:曹文轩 著
- ISBN:9787556087471
- 版次:1
- 包装:平装
- 出版社: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出版时间:2018-10-01
- 丛书名:
- 开本:32开
- 套装数量:
- 外文名称:
- 页数:202
- 正文语种:中文
- 字数:
评分
内容简介
编辑推荐
★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力作。
★一部关于信任、勇气、感恩的长篇小说,一个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动物故事。
★曹文轩首部动物小说。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长篇小说,也是作者首部以狗为题材的作品。故事发生在北方的一个海边渔村,小女孩船花收养了一条白色的小母狗,取名沫沫。船花待沫沫如同家人,吃饭睡觉都跟它一起。沫沫对船花也忠心耿耿,保护着船花不受村里孩子的欺负。一次偶然,沫沫误入一片树林,被盘踞在此的一群流浪狗围困。被疯狗浪卷上岸边的大公狗黑风,帮助沫沫摆脱了群狗的纠缠,自己却因此身受重伤。沫沫将黑风带回家,细心照料。船花一家虽然生活拮据,还是接受了黑风。但流浪狗的首领狼脸一直耿耿于怀,通过阴险的离间计,使得黑风被赶出家门。而沫沫毅然选择了跟黑风一起出走。它们困守荒山,顽强地与群狗周旋,在一起度过了一段艰苦又甜蜜的时光,沫沫也幸福地当了母亲。而狼脸一直带领群狗围困在山下。为了将沫沫和孩子们送回船花身边,黑风勇敢地牺牲了自己。当沫沫带着孩子回到村子里时,却发现船花已经重新养了一条白色的狗。伤心和绝望之下,沫沫带着孩子走进树林,加入了流浪狗的队伍。
作者简介
曹文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埋在雪下的小屋》《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天瓢》《红瓦》《根鸟》《细米》《青铜葵花》《大王书》《我的儿子皮卡》《火印》《蜻蜓眼》等,另有绘本《飞翔的鸟窝》《羽毛》《柏林上空的伞》等二十余种。《红瓦》《草房子》《青铜葵花》等被译为英、法、德、希腊、日、韩、瑞典、丹麦、葡萄牙等文字。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文学奖、冰心文学大奖、国家图书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金蝴蝶奖等重要奖项四十余种。2016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作家。
目录
一 流浪狗的王国
二 黑风
三 沫沫
四 收留
五 羊圈里的秘密
六 黄毛三根
七 沙丘上的狼脸
八 陷害
九 光秃秃的小山
十 它像一个王者
十一 风整整吼了一夜
十二 偷窃
十三 魔鬼都要绕着走
十四 黑白花
十五 被劫走的花花
十六 别了,船花
精彩书摘
一 流浪狗的王国
沫沫去村东头长毛家玩了半天,突然想起小主人船花还在家中,赶紧一溜烟跑回家。
门锁着,船花不在。
她去哪儿了呢?
沫沫“汪汪”叫唤了两声,见还是没有船花的身影,就满村子找开了――依然没有船花的身影。
她到底去哪儿了呢?
沫沫有点儿急了。船花的爸爸妈妈出海捕鱼时,叮嘱了它好几遍呢:“守护好船花。”可是现在却不见船花的人影了。它一边跑,一边“呼哧呼哧”地喘息着。它后悔自己丢下船花去找长毛玩了――玩就玩吧,还一玩就是半天!
它满村子又找了一遍。
这时,太阳已经没有多高了。
它到哪里去找船花,船花这时已在外婆家了。中午,舅舅路过这儿,知道船花的爸爸妈妈出海捕鱼去了,要到后天才能回来,就将船花带走了。船花离开时,曾到处找过沫沫,却没找到。找不到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也不能带它一起去外婆家,它还要看家呢。船花只是想对它说一声:“我去外婆家了,你好好看家。”
外婆家离这儿几十里地。
沫沫根本想不到船花会去外婆家。眼见着太阳像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拖拽着越来越低,沫沫看着西边的天空,在喉咙里呜咽起来。
它回头看了一眼锁着的门,往海滩跑去。
船花很喜欢跑到海滩上玩,特别是当爸爸妈妈出海捕鱼时,更喜欢跑到海滩上,一边玩,一边在那里等爸爸妈妈从海上回来。沫沫已无数次地陪着船花,眺望大海。那时,船花坐在海边的一块岩石上,它就蹲在她的身旁。海浪从海上一波一波涌来,“哗啦,哗啦”,永远一个节奏地响着。
静静地眺望。
它会向船花靠紧一点。它感觉到,船花很喜欢它紧紧地挨着她。
大海一片苍茫。
船花会把它抱到怀里……
沫沫一边心里想着船花,一边快速跑向海滩。天气干燥,地面上是一层浮土,沫沫跑过,身后是一溜扬起的尘埃,像是一条黄色的、扭动着身子的怪物。
眼前就是大海。
沙滩空无一人,那块岩石上也空空的。
海浪排排,一排赶着一排,向岸边扑来。风不大,浪不高。扑到岸边时,只是激起三四尺高的浪花。这里浪花落下,又有新的浪花忽地开放。落下,开放,无休无止。
海的声音,由远及近,如同呼吸之声。
几只海鸥低空盘旋在海浪之上,在太阳落下之前,它们还想从海浪中再吃到几条小鱼。
明明没有船花的影子,但沫沫还是向大海跑了过来,一直跑到水边。水漫上沙滩,它的四腿立即被海水淹没一半。它一惊,跳了起来,随即往回跑了一阵。但它并没有返回村庄,而是沿着海岸,一路向西跑去。
西边有一片树林。它曾在船花的带领下,去过那边。但,那已是很久之前的事了。船花会不会去那儿呢?它不停地跑着,不住地在心里责备自己。
在距离这片树林还有几十米远的地方,沫沫停下了。
它望着这片树林。这片树林不算小,因为沙丘起伏,这片树林也是起伏的。沫沫停下,是因为,它总觉得这片树林凉飕飕、阴森森的。那次,它随船花来到这片树林,并没有进去,差不多就在它现在站的地方站住了,向树林里张望着。沫沫还记得当时的情景:秋风从海上吹来,吹得眼前的树都在摇晃,梢头“呜呜”作响;林子深处,不知是什么动物,叫唤了一声,像鸟声,又不像鸟声,反正它以前从没有听到过这样怪异的声音。它禁不住叫了一声。它这么一叫,船花更显得惶惶不安了,一边看着这片树林,一边后退着――退了五六步,扭过头去,拼命往回跑,一边跑,一边叫着:“沫沫!沫沫!……”它没有立即掉头跑,蹲在地上,依然看着树林。船花见没有沫沫的动静,回过头来,大声地叫着:“沫沫!”它这才向船花跑去。
就这一回,后来,它和船花再也没有来过这儿。
沫沫蹲在那儿,望着这片树林。她不会独自一人来这儿吧?可是,我什么地方都找过了呀!沫沫还是望着这片树林,它甚至想到,船花会不会到林子里面去玩了呢?这么一想,它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它不再蹲在那儿,而是四腿立着站在那儿,用它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向林子深处看去――日光已暗,什么也看不见。它的四条腿,轮换着,不安地来回抬起,落下。
沫沫根本不会想到,它已处在高度的危险之中。
这片林子,现在已成为一群流浪狗的王国。这些流浪狗并不是本地狗。听说,流浪狗会成群结队地不停奔走,能一路流浪走到千里之外。这群流浪狗来自何处,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它们自己大概也说不清楚。但是,自从走进这片林子之后,它们的行走,就结束了。它们有一种来到天堂的感觉。多好的一片林子呀!很少有人来打扰,既安静又安全。白天它们尽量待在林子深处,到了夜晚,它们就会走出林子,沿着海边往前奔跑。月光下,它们会不时地看到被海浪冲到沙滩上的鱼,它们可以在饥饿了一天之后,好好美餐一顿。即使没有月光,它们也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被海浪冲到沙滩上的鱼。有时候,它们也会在夜深人静之时,流窜到一些村庄,找些其他食物――总吃鱼,未免也太单调了一些。它们几乎不叫唤,常年流浪,让它们养成了沉默的习惯。因为叫声会给它们带来太多的麻烦。现在,它们不像狗,更像鬼鬼祟祟的狼。它们在这片树林里住下,已经有一些时候了,可是,沫沫从来没有见到过它们其中任何一条的身影。
当沫沫还在向这片林子跑来时,它们中间那只叫“吊眼”的灰狗,就已经看到了它。吊眼立即跑向林子的最深处。它要立即将情况报告给它们的首领――那只叫“狼脸”的棕色的狗。
前言/序言
文学:另一种造屋
我为什么要――或者说我为什么喜欢写作?写作时,我感受到的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一直在试图进行描述。但各种描述,都难以令我满意。后来,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确切的、理想的表达:写作便是建造房屋。
是的,我之所以写作,是因为它满足了我造屋的欲望,满足了我接受屋子的庇荫而享受幸福和愉悦的欲求。
我在写作,无休止地写作:我在造屋,无休止地在造屋。
当我对此“劳作”细究,进行无穷追问时,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造屋的情结,区别也就是造屋的方式不一样罢了――我是在用文字造屋:造屋情结与生俱来,而此情结又来自于人类最古老的欲望。
记得小时候在田野上或在河边玩耍,常常会在一棵大树下,用泥巴、树枝和野草做一座小屋。有时,几个孩子一起做,忙忙碌碌,很像一个人家真的盖房子,有泥瓦工、木工,还有听使唤的杂工。一边盖,一遍想象着这个屋子的用场。不是一个空屋,里面还会放上床、桌子、书柜等家什。谁谁谁睡在哪张床上,谁谁谁坐在桌子的哪一边,不停地说着。一座屋子里,有很多空间分割,各有各的功能。有时好商量,有时还会发生争执,最严重的是,可能有一个霸道的孩子因为自己的愿望未能得到满足,恼了,突然一脚踩烂了马上就要竣工了的屋子。每逢这样的情况,其他孩子也许不理那个孩子了,还骂他几句很难听的,也许还会有一场激烈的打斗,直打得鼻青脸肿“哇哇”地哭。无论哪一方,都觉得事情很重大,仿佛那真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屋子。无论是希望屋子好好地保留在树下的,还是肆意要毁坏屋子的,完全把这件事看成了大事。当然,很多时候是非常美好的情景。屋子盖起来了,大家在嘴里发出“噼里啪啦”一阵响,表示这是在放庆贺的爆竹。然后,就坐在或跪在小屋前,静静地看着它。终于要离去了,孩子们会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很依依不舍的样子。回到家,还会不时地惦记着它,有时就有一个孩子在过了一阵子后,又跑回来看看,仿佛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家,到外面的世界去流浪了一些时候,现在又回来了,回到了他的屋子、他的家的面前。
我更喜欢独自一人盖屋子。
那时,我既是设计师,又是泥瓦工、木匠和听使唤的杂工。我对我发布命令:“搬砖去!”于是,我答应了一声:“哎!”就搬砖去――哪里有什么砖,只是虚拟的一个空空的动作,一边忙碌一边不住地在嘴里说着:“这里是门!”“窗子要开得大大的!”“这个房间是爸爸妈妈的,这个呢――小的,不,大的,是我的!我要睡一个大大的房间!窗子外面是一条大河!”……那时的田野上,也许就我一个人。那时,也许四周是滚滚的金色的麦浪,也许四周是正在扬花的一望无际的稻子。我很投入,很专注,除了这屋子,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那时,也许太阳正高高地悬挂在我的头上,也许很快落进西方大水尽头的芦苇丛中了――它很大很大,比挂在天空中央的太阳大好几倍。终于,那屋子落成了。那时,也许有一支野鸭的队伍从天空飞过,也许,天空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就是一派纯粹的蓝。我盘腿坐在我的屋子跟前,静静地看着它。那是我的作品,没有任何人参与的作品。我欣赏着它,这种欣赏与米开朗基罗完成教堂穹顶上一幅流芳百世的作品之后的欣赏,其实并无两样。可惜的是,那时我还根本不知道这个意大利人――这个受雇于别人而作画的人,每完成一件作品,总会悄悄地在他的作品的一个不太会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名字。早知道这一点,我也会在我的屋子的墙上写上我的名字的。屋子,作品,伟大的作品,我完成的。此后,一连许多天,我都会不住地惦记着我的屋子,我的作品。我会常常去看它。说来也奇怪,那屋子是建在一条田埂上的,那田埂上会有去田间劳作的人不时地走过,但那屋子,却总是好好地还在那里。看来,所有见到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直到一天夜里或是一个下午,一场倾盆大雨将它冲刷得了无痕迹。
再后来就有了一种玩具――积木。
那时,除了积木,好像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玩具了。一度,我对积木非常着迷――更准确地说,依然是对建造屋子着迷。我用这些大大小小、形状不一、颜色各异的积木,建造了一座又一座屋子。与在田野上用泥巴、树枝和野草盖房子不同的是,我可以不停地盖,不停地推倒再盖――盖一座与之前不一样的屋子。我很惊讶,就是那么多的木块,居然能盖出那么多不一样的屋子来。除了按图纸上的样式盖,我还会别出心裁地利用这些木块的灵活性,盖出一座又一座图纸上并没有的屋子来。总有罢手的时候,那时,必定有一座我心中理想的屋子矗立在床边的桌子上。那座屋子,是谁也不能动的,只可以欣赏。它会一连好几天矗立在那里,就像现在看到的一座经典性的建筑。直到一只母鸡或是一只猫跳上桌子毁掉了它。
现在我知道了,屋子,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就会有的意象,因为那是人类祖先遗存下的意象。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堂美术课老师往往总是先在黑板上画上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再用几条长长短短、横着竖着的直线画一座屋子的原因。
屋子就是家。
屋子的出现,跟人类对家的认知联系在一起的。家就是庇护,就是温暖,就是灵魂的安置之地,就是生命延续的根本理由。其实,世界上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都是和家有关的。幸福、苦难、拒绝、祈求、拼搏、隐退、牺牲、逃逸、战争与和平,所有这一切,都与家有关。成千上万的人呼啸而过,杀声震天,血沃沙场,只是为了保卫家园。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像高高的槐树顶上的一个鸟窝不可侵犯一样。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的一个情景:一只喜鹊窝被人捅掉落在了地上,无数的喜鹊飞来,不住地俯冲,不住地叫唤,一只只都献出不顾一切的样子,对靠近鸟窝的人居然敢突然劈杀下来,让在场的人不能不感到震惊。
家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
当我终于长大时,儿时的造屋欲望却并没有消退――不仅没有消退,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生感悟的不断加深,而愈加强烈。只不过材料变了,不再是泥巴、树枝和野草,也不再是积木,而是文字。
文字建造的屋子,是我的庇护所――精神上的庇护所。
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无论是抒发,还是安抚,文字永远是我无法离开的。特别是当我在这个世界里碰得头破血流时,我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我的家。虽有时简直就是铩羽而归,但毕竟我有可归去的地方――文字屋。而此时,我会发现,那个由钢筋水泥筑成的物质之家,其实只能解决我的一部分问题而不能解决我全部的问题。
还有,也许我如此喜欢写作――造屋,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满足了我天生想往和渴求自由的欲望。
这里所说的自由,与政治无关。即使最民主的制度,实际上也无法满足我们自由的欲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参与者的萨特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听上去让人感到非常刺耳,甚至令人感到极大的不快。他居然在人们欢庆解放的时候说:“我们从来没有拥有比在德国占领期更多的自由。”他曾经是一个革命者,他当然不是在赞美纳粹,而是在揭示这样一个铁的事实:这种自由,是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都无法给予的。在将自由作为一种癖好,作为生命追求的萨特看来,这种自由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但他找到了一种走向自由的途径:写作――造屋。
人类社会如果要得以正常运转,就必须讲义务和法则,就必须接受无数条条框框的限制。而义务、法则、条条框框却是和人的自由天性相悖的。越是精致、严密的社会,越要讲义务和法则。因此,现代文明并不能解决自由的问题。但自由的欲望,是天赋予的,那么它便是合理的,是无可厚非的。对立将是永恒的。智慧的人类找到了许多平衡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写作。你可以调动文字的千军万马。你可以将文字视作葱茏草木,使荒漠不再。你可以将文字视作鸽群,放飞无边无际的天空。你需要田野,于是就有了田野。你需要谷仓,于是就有了谷仓。文字无所不能。
作为一种符号,文字本是一一对应这个世界的。有山,于是我们就有了“山”这个符号。有河,于是我们就有了“河”这个符号。但天长日久,许多符号所代表的对象已不复存在,但这些符号还在,我们依然一如往常地使用着。另外,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叙述,常常是一种回忆性质的。我们在说“一棵绿色的小树苗”这句话时,并不是在用眼睛看着它,用手抓着它的情况下说的。事实上,我们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实在用语言复述我们的身体早已离开的现场,早已离开的时间和空间。如果这样做是非法的,你就无权在从巴黎回到北京后,向你的友人叙说卢浮宫――除非你将卢浮宫背到北京。而这样要求显然是愚蠢的。还有,我们要看到语言的活性结构,一个“大”字,可以用它来形容一只与较小的蚂蚁相比而显得较大的蚂蚁――大蚂蚁,又可以用它来形容一座白云缭绕的山――大山。一个个独立的符号可以在一定的语法之下,进行无穷无尽的组合。所有这一切都在向我们诉说一个事实:语言早已离开现实,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这个王国的本质是自由。而这正契合了我们的自由欲望。这个王国有它的契约。但我们可以在这一契约之下,获得广阔的自由。写作,可以让我们的灵魂得以自由翱翔,可以让我们自由之精神,得以光芒四射。可以让我们自由向往的心灵得以安顿。
为自由而写作,而写作可以使你自由。因为屋子属于你,是你的空间。你可以在你构造的空间中让自己的心扉完全打开,让感情得以充分抒发,让你的创造力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而且,造屋本身就会让你领略自由的快意。房子坐落在何处,是何种风格的屋子,一切,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当屋子终于按照你的心思矗立在你的眼前时,你的快意一定是无边无际的。那时,你定会对自由顶礼膜拜。
造屋,自然又是一次审美的历程。房子,是你美学的产物,又是你审美的对象。你面对着它――不仅是外部,还有内部,它的造型,它的结构,它的气韵,它与自然的完美合一,会使你自然而然地进入审美的状态。你在一次又一次的审美过程中又得以精神上的满足。
再后来,当我意识到了我所造的屋子不仅仅是属于我的,而且是属于任何一个愿意亲近它的孩子时,我完成了一次理念和境界的蜕变与升华。再写作,再造屋,许多时候我忘记了它们与我的个人关系,而只是在想着它们与孩子――成千上万的孩子的关系。我越来越明确自己的职责:我是在为孩子写作,在为孩子造屋。我开始变得认真、庄严,并感到神圣。我对每一座屋子的建造,殚精竭虑,严格到苛求。我必须为他们建造这世界上最好、最经得起审美的屋子,虽然我知道难以做到,但我一直在尽心尽力地去做。
孩子正在成长过程中,他们需要屋子的庇护。当狂风暴雨袭击他们时,他们需要屋子。天寒地冻的冬季,这屋子里生着火炉。酷暑难熬的夏日,四面窗户开着,凉风习习。黑夜降临,当恐怖像雾在荒野中升腾时,屋子会让他们无所畏惧。这屋子里,不仅有温床、美食,还有许多好玩的开发心智的器物。有高高矮矮的书柜,屋子乃为书,而这些书为书中之书。它们会净化他们的灵魂,会教他们如何做人。它们犹如一艘船,渡他们去彼岸;它们犹如一盏灯,导它们去远方。
对于我而言,我最大的希望,也是最大的幸福,就是当他们长大离开这些屋子数年后,他们会时不时地回忆起曾经温暖过、庇护过他们的屋子,而那时,正老去的他们居然在回忆这些屋子时有了一种乡愁――对,乡愁那样的感觉。这在我看来,就是我写作――造屋的圆满。
生命不息,造屋不止。既是为我自己,更是为那些总让我牵挂、感到悲悯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