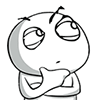儿子4岁的时候,陈女士的焦虑达到了巅峰,而这种焦虑是从为自己的儿子选童书开始的。
为了给儿子买到合适的童书,她加入了一些购书的微信群和QQ群,原来里面都是一些给自己孩子囤书的年轻妈妈。几天之后,她见识到了妈妈们的威力和焦虑。她们从早上7点开始,到夜里1点,都在群里分享抢图书优惠券和买书经验。看了一眼她们晒出来的书单,大概从甲骨文丛书到外国的儿童百科全书都囤起来了。
“这些都是名家推荐的,先买了囤着,总会有用的。”那些妈妈买的书都是自己没有读过的,不知道从哪风闻一些广告,就大肆囤书。这让陈女士瞠目结舌。
数据显示,2016年国内图书市场上针对少儿的图书多达15.28万种,“选书难”是近年来促使“分级阅读”呼声渐高的原因之一,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6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为儿童挑选图书时,56.0%的受访者感到困难,72.7%的受访者表示需要国家有关方面制定参考标准。
分级书单不能像“土郎中”开补药
在焦虑重压下,陈女士将目光投向一些社会上“名家”“名机构”推荐的分级书单。每天在群里,陈女士都会收到四五份书单,让她生疑的是,很多书单里推荐的图书都存在着冲突。“在不同的书单里,《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一会儿是三年级必读,一会儿又变成五年级必读。这本书到底适合几年级的孩子看?”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阅读与学习研究中心主任伍新春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对目前3种书单做了阅读难易度的分析。这3张书单,不乏名校校长和知名机构的推荐,分析后呈现出的是3张曲折攀升的“折线图”。这意味着这3张书单,并不完全符合儿童的认知发展规律和阅读能力,每一段折线“下潜”意味着这一阶段推荐的书“过于简单”,孩子感到吃不饱。每一段折线的陡然上升则意味着,这些书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难度太大。
“这些书单更多的是根据经验的标准选择图书,而非科学。”在伍新春看来,这是目前研究儿童阅读的一个困境。“研究儿童阅读的人基本上都是语文背景或者文学背景,他们缺乏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专业背景,基于文本的视角去考虑,而不是基于孩子的视角去考虑。”
伍新春打了一个比方,“现在一堆的书单,就相当于各种各样的补药,而很多推荐者就像‘土郎中’,总是把他们认为效果好的补药开给孩子。但实际上,这些药并不适合孩子”。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认为,分级阅读主要是针对儿童不同年龄段身体、智力、知识和状态提出的概念,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共同完成。
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推广面向儿童的图书分级制,为不同年龄儿童提供适合其年龄特点的图书,为家长选择图书提供建议和指导。这被视为儿童分级阅读的方向,但其并未对“分级制”提出更详细的方案。
早在100多年前,欧洲就已经开始研究儿童分级阅读的问题。目前国外比较知名的分级体系中知名度最高、应用最广泛的就是“蓝思分级阅读体系”,全球超过180个国家都在使用蓝思阅读能力测评服务。美国每年有超过3500万的中小学生使用蓝思分级来衡量自己的阅读水平和选择合适的图书,加拿大、英国、德国等20多个国家使用蓝思建立了英语阅读能力培养的量化指标。
据伍新春介绍,蓝思系统对读物的分级主要是依据词义难度(词汇)和句型复杂度。蓝思分析系统先仔细考察与整体阅读理解力相关的各项元素,如句子长度、单词出现的频率等,然后再通过计算,确定一个读物的难易程度,并确定其对应的蓝思值。比如,《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蓝思值为880L。
不过,中国的中文分级阅读其实早已起步,2008年,南方分级阅读研究中心成立,针对3至18岁青少年儿童的阅读现状,提出了分级阅读理念。如今,分级阅读概念已经走向实践层面。陈女士在某个电商平台发现,其推出的“陪伴计划”就是针对育有孩子的家庭,将童书贴上近百种标签,以年龄和性别维度对用户、商品、内容精准匹配。
儿童文学作家、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在接受采访时说,儿童分级阅读在中国刚刚起步,这种初级阶段的表现是研究机构少,而且大多是民间机构,实力不强,资源有限。现在少年儿童出版界虽然越来越重视分级创作、分级策划、分级出版、分级推广、分级展示,但这种分级是基于对儿童读者年龄的粗浅划分,带有很大的分级者的主观色彩,而不是以儿童读者为主体、以儿童阅读能力为基准的科学的分级。
阅读分级更像是自行车的“辅助轮”
不过,这套覆盖全美75%中小学的分级阅读系统,并非完美无缺。因为仅从词汇和句子长度去判断一本书是否适合孩子阅读,是欠考量的。
比如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ohn Steinbeck的小说《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蓝思值为680L,与《夏洛的网》(Charlotte’s Web)相同,但是书中充满人的冲突、宗教的隐喻,思想内容与《夏洛的网》不可同日而语,也不是孩子可以理解的。
不仅如此,中国的分级阅读体系迟迟没能建立起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渐高的呼声相对的质疑声。
这样的质疑其实并不难理解,有专家说:“孩子的理解能力就是天然的阅读过滤器,是天然的分级能手,不需要再依靠外部力量去对童书进行分级”。
儿童文学作家保冬妮认为,从阅读实践出发,7岁以后的阅读水平,视儿童在6岁前阅读习惯的建立与否,开始逐渐拉开距离。这个时期开始分级会限制大部分阅读能力强的孩子,因为就小学中高年级的自主阅读而言,能力强的孩子,阅读的文本已经与成人大致相同。
分级阅读,如同童车上的辅助轮,一旦学会了骑车,辅助轮就可以被拆掉了。
在讨论建立分级阅读标准的过程中,“借鉴”是一个高频词。目前,咿啦看书已与蓝思达成合作,成为大陆首家获得授权的中国儿童数字阅读平台。尽管如此,咿啦看书创始人任晖也认为,中国的分级阅读体系不能简单照搬蓝思。
任晖认为,中文分级面临的困难重重,“中文的语言结构和英文非常不同,很难量化评估。对中文的评估同时还要考虑儿童的心理和生理、社会和区域的长期影响等多方面因素,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从研究资源的角度看,中文分级阅读的标准和框架的开发与制定需要大量时间、实际研究样本、人力物力,所以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个课题。”
同时,从领域协作的角度看,统一这个概念特别难,出版社、研究机构、阅读推广人、童书作者、大众市场等,各个研究阅读领域的专业人士会有自己不同的角度和观点,要去整合各方渠道开发一套标准体系,这很有难度,而目前还没有达到资源共通的程度。
在白冰看来,儿童分级阅读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对文本难度的评估,到底哪些因素会影响文本难度?字、词、主题思想、文本长短、文图搭配等等,这些变量如何平衡?中文阅读是不是可以像国外一样,设计出一个“难度公式”,通过某种程度的计算,测定一个文本的难度?另一个层面是阅读主体——儿童阅读能力的评估。中国儿童的阅读能力如何评估?面对中国城乡、地区、学校、家庭和儿童个体的巨大差异,这都需要通过大量的数据调查,建立数据模型,来测定儿童阅读能力标准。
伍新春说,中文分级阅读的核心并不在于开药方,而在于诊断。伍新春及其研究团队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研发出了“SLARE学生阅读与学习能力测评体系”。该测评体系建立在相关阅读理论基础上,主要从直接提取、直接推论、解释并整合观点和信息、检视并评价内容、语言和文本成分等方面考查学生的阅读能力。测试结果可反映出学生从文本中建构意义的一系列技能,从而助力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学习能力的发展和必备素养的提升。
“儿童之选”还是“成人之选”
在给儿子选书的过程中,最让陈女士感到挫败的是,自己选的大部分书,儿子都不感兴趣。
困扰群里很多妈妈的问题,被一个孩子一语道破,如果说有一种冷,叫作“我妈妈觉得我冷”,那么就有一种书,叫作“我妈妈觉得我爱看的书”。
在北师大实验小学,伍新春带着这里的语文教师们做了一项“无为而治”的阅读实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就是让学生自己选书,而非家长或者教师选书。
“不放心”这几乎是一开始教师们跟伍新春抱怨最多的话,他们担心这样的阅读课会变成放羊课。在伍新春看来,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孩子们自选的书目是已经过挑选的,教师们的担心其实在某个程度上是打着“儿童为中心”旗号的“成人立场”。“不放心”的心态,背后是“学科教学”的思维和功利性读书的心态在作祟。
“不检查,不考试,教师陪读”这样一个学期过后,学生反而爱上了阅读。
伍新春说:“让孩子真正爱上阅读的途径是在对阅读进行分级之后,给孩子足够的选择权。比如说,我们语文教材里面每一篇选文都是专家们精挑细选的,却很少有孩子会看得如痴如醉。但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书,却很容易。”
实际上,在美国,除了享誉盛名的纽伯瑞和凯迪克大奖这样纯粹由成人定夺的童书奖以外,还有儿童之选书单和儿童之选童书奖,这两个奖项是在美国范围内数以百万计的在校少年儿童在网上投票决出的。
除了让学生自主选择喜欢的书以外,吸引学生爱上阅读还有一个原因,伍新春说:“那就是同伴阅读。”
从目前儿童阅读开展的态势来看,由于社会、政府的提倡,“亲子阅读”可谓是占据了儿童阅读推广的主流,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阅读激励和协作方式:同伴阅读。往往我们的阅读书目或阅读品位,跟所在的群体关联极大。
伍新春说:“尤其是青春期以后,同辈群体的作用更大,同伴阅读对于落实最近发展区、增强阅读的效能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这样阅读上的互动和激励对于人格的完善和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